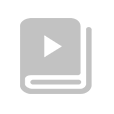唐代是国内诗歌艺术最为兴盛发达的一个年代,从初唐到盛唐再到晚唐,诗歌这一文学体式渐渐成熟,在格律,语汇,修辞,音韵上都有了崭新的创造,为后世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参照。李泽厚先生在《美的经历?盛唐之音》中说到绝句的时尚,称其为“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①之一,本文凑合盛唐绝句的形式更为具体全方位地探讨一下其时尚的美学依据。
1、字数限制有益于激起想象
诗人在创造诗篇时,势必要经过艺术化的“想象”,即“回想或凑合以往意象的心理活动”③。绝句与其他诗体相比,篇章很短小,五绝或七绝,字数不过20字或28字。要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创造出出色的作品,诗大家需要要更多地运用想象手法,用分想从繁冗的意象中筛选自己需要的,用联想手法“托人”或“托物”,在有限的篇幅里把要表达的情感和作品的美感最大化地呈现,并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目前大家看到的不少绝句名篇,都是通过想象用途,“以小见大”,“托物寓端”④,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充满飘逸灵动之感的,王昌龄诗中的“玉颜不及寒鸦色”“一片冰心在玉壶”就非常不错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2、四句一篇的结构美
绝句又称截句,断句,其篇幅只有律诗的一半。律诗八句,绝句四句,这种四句一篇的结构具备独特的美感。国内古时候的抒情短诗,民谣多为四句一体,《诗经》中多为四句一章,再反复重叠成篇(如《硕鼠》)。《楚辞》里多四句为一完整的叙事或抒情单位(如屈原《离骚》)。汉魏六朝的乐府诗歌也多这样。“四句既短小自然,而又完整平衡,与中国古时候诗歌基本的审美趣味也是合拍的”,“更能体现大家抒情的自然特征”⑤,具备天然的结构美感。此外,四句短小,易于背诵与传播,流传范围会更广,时间也会更长久,因此在盛唐时期广为时尚,直到今天日依旧在每人耳熟能详的唐宋名篇里占据着绝大多数。
3、较为灵活的格律运用使其与诗人和受众维持了适合的“心理距离”
绝句于唐代开始律化,格律的用法使诗歌与创作者和受众间产生一种“心理距离”,使之与普通生活不同开来,成为一种能使人赏析的艺术。
这种“心理距离”对创作者带来有哪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格律的用法可以帮助作者从感情出发又跳脱于感情以外,“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在自己和这感情之中辟出一个距离来”⑥。诗人在做诗的时候,除去表达感情的需要,还要考虑到格律上的限制(虽然格律由大家长久的语言习惯演化而成,内在地有一种情感的规律),考虑音节韵律,“章句长短”与“平仄交错”⑦。因此诗人感情的涌动和诗歌创作之间会历程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反刍与构思过程,“炼字”也就成为一种要紧技法。这种时间差有益于诗人从强烈的感情中抽离出来,对情绪进行艺术的再创造。第二,格律的用法能把日常与实用关联太密的东西放在适当的“心理距离”上,让好用的,离生活太近的事物重新拥有美感。朱光潜先生在《文静心理学》中说韵文比散文距离实质生活更远,《关雎》才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绝句句式齐整,音韵和谐,在形式上可以自然地把实用性的人事与实质生活拉开距离,使其带出别样的美感。绝句内容的涵盖面就会更广,在社会上也会有更高的时尚度。除此之外,绝句格律的不完全性使它与同意者间的“心理距离”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有益于一般民众的同意。绝句不同于一般格律诗的地方是它可以遵循格律,是为律绝,也可以不完全遵循格律,是为古绝。盛唐时期的绝句创作二者兼有之,如此就使绝句有了一定量上的形式自由度。对诗大家的束缚小了,创作量就大;诗句愈加通俗易懂,传播面就广。就像朱光潜先生在《文静心理学》里说的那样,距离太远了(太过形式化)不容易于观赏者知道引发其兴趣,距离太近了实用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绝句就是这种“不即不离”艺术的绝妙体现。
4、绝句的形式可以入乐而产生音乐美
绝句本身由于格律,押韵方面是什么原因,就携带自然的音乐美,再加上唐人绝句形式与乐府的关系非常近,大都可以入乐演唱,就更增加了绝句的音乐美。唐人以绝句充当歌词配合新的乐曲,大诗人刘禹锡就创作了一系列可以入乐演唱的《竹枝词》,步伐明快,朗朗上口。音乐大都可以引起听者的移情现象,听到高昂急促的音乐时大家会感觉昂扬欢快,听到低沉缓慢的音乐时大家会感觉伤心难过,加上绝句的配合成效就会愈加明显。因此绝句形式可以入乐演唱所产生的音乐美,也是它引起民众共鸣与诗人创作热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盛唐绝句字数限制激起的想象,四句一篇致使的结构美,格律的灵活运用产生的“不即不离”的“心理距离”与可以入乐引发的音乐美使其在盛唐时期广为时尚,艺术收获也达到了这一诗歌体式的顶峰。